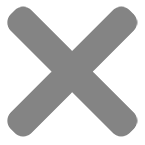我大喊:「殺!殺!」一直喊到喉嚨沙啞了才停。我們在刺刀對打與徒手搏擊課程時,一定會喊「殺!殺!」我們行進時,也會唱類似的歌:「我要當一名空降遊騎兵……我要殺越共。」我十六歲就不殺小動物了。我那時打傷了一隻松鼠,再補一槍幫牠解脫時,牠在地上用兩隻黃褐色、溫柔的大眼睛看著我。我把槍清乾淨以後,就再也沒有拿出來過。到了一九六九年我被選中(到越南),心中忐忑不安。我也不關心越共到底做了什麼。但是等到基本訓練結束時,我覺得自己已經準備好、隨時可以殺他們了。
——傑克,越戰老兵
軍方使用的古典制約方法
華生(P. Watson)在其著作《控制心靈的戰爭》(War on the Mind)所揭露的秘辛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當年曾經以制約方法訓練殺手。美國海軍的精神科醫生納魯特(Dr. Narut)中校告訴華生關於他運用古典制約與社會學習,訓練軍方殺手克服對殺人的抗拒心理。納魯特說,這種訓練的執行方式是將訓練對象置入「象徵模仿」(symbolic modeling)的情境中,包含「觀看以激烈暴力方法殺人或傷害人的特製影片。這些儲備殺手一開始會感覺強烈不適,而訓練的目的是他們最終能把自己的情緒與影片呈現的情境分離。」
納魯特接著說:「這些人除了學習射擊之外,還接受一種特殊的的訓練,目的是降低殺人產生的不舒服感覺。他們的頭部被夾具固定,因此無法轉動,眼皮則用一種特殊工具撐開,因此無法閉眼。然後以噁心程度逐漸升高的順序,放映一系列毛骨悚然的影片,強迫他們觀看。」用心理學的術語來說,這種逐步降低抗拒的方法,就是一種稱為「系統性減敏感」的古典(帕伏洛夫)制約方式。
《發條橘子》這部電影中呈現的制約方式,是在主角觀看暴力電影時注射會產生噁心感覺的藥物,製造厭惡與暴力之間的關聯,最後達到當事人對暴力產生厭惡感的目的。但是納魯特中校的訓練並沒有使用會產生噁心感覺的藥物,相反的,受訓學員若是能克服自己天生的噁心感,則會得到獎賞。因此,他的訓練達到的效果剛好與電影呈現的情節相反。美國政府否認納魯特中校的說法,但是華生透漏,有另一位人士告訴他,納魯特向這位人士訂購了一批暴力電影,由此第三方證據可證明納魯特的說法為真。倫敦泰晤士報後來也報導了納魯特的故事。
請記得,減敏感是現在作戰訓練項目中運用在殺人賦能的一個重要元素。本章一開始引述越戰老兵傑克的經驗,就是減敏感與讚美殺人的例子,這種方法也逐漸成為作戰基礎訓練的一部分。我在一九七四年進行基本訓練時,就唱過很多類似的軍歌與答數。其中一個只比其他大部分答數更極端一些的連續答數是這樣唱的(左腳踏地時喊一句):
我要姦殺搶,和燒,
還要吃掉死嬰。
我要姦殺(以下連續重複)
美軍現在禁止以這種方式減敏感,但是數十年來這種方式是在基本訓練期間,將男性青少年減敏感與教導他們狂熱追求暴力的主要機制。

電影中的古典制約
如果我們認為納魯特中校的訓練方式有可能收到效果,如果我們對美國政府甚至考慮過對我們的士兵進行這種訓練感到厭惡,那麼,我們為什麼可以容許全國數以百萬的孩子也經歷同樣的制約過程?當我們讓愈來愈生動的痛苦與暴力情節以娛樂之名讓我們的孩子觀賞時,不就是在容許他們經歷同樣的過程?
這一切從純真無邪的卡通開始。隨著孩子長大,電視上也出現數不清、無數的暴力畫面,接著暴力的門檻因為電視競相追逐收視率而逐漸降低。等到孩子到了一定年紀,就可以到電影院觀看列為PG-13級的電影,因為這些電影裡面只出現一點點濺血、被砍下的肢體或是子彈傷口等一定程度的暴力情節,符合PG-13的分級標準。接著呢,父母或因疏忽、或甚至也願意讓孩子觀看R級電影。這些電影因為含有肢體分離、噴血的長鏡頭,或有刀子刺穿身體,或子彈從身體後方穿出、傷口爆裂、血液與腦漿四濺的鮮活畫面,因而被列為R級電影。
最後,我們的社會規定,青少年十七歲的時候可以合法觀看這些R級電影(雖然大部分青少年早在十七歲前就看過了),到了十八歲則可以觀看比R級限制更嚴格的電影。在這些電影中,多半時候,出現栩栩如生的挖眼珠畫面還算是最不噁心的小兒科情節。十七、八歲這段可塑性最高的年紀,正是傳統上軍方對士兵施行殺人教育的時段,而從小就在系統減敏感環境下長大的美國青少年,也同樣在這個年紀進一步接受了暴力文化的洗禮。
在這種令人毛骨悚然、恐怖畫面愈來愈鮮明的「娛樂」裡的反英雄,例如吃人魔漢尼拔、傑森和佛萊迪,都是一群病態、殺不死的人,沒人懷疑他們是邪惡的,他們的反社會人格也應該被處以刑罰,但這種娛樂卻環伺在我們的青少年與成人周遭。這些角色與早一代的恐怖電影中具有異國情調、神秘、又遭人誤解的壞人角色如科學怪人、狼人完全不同。早期的恐怖故事與電影製造的恐懼是雖然非常真實,但卻藏在潛意識中,而且是靠著如德古拉伯爵這種存在於神話中、不真實的角色具象化,然後再安排一支木樁穿刺心臟的情節,神奇的將恐懼「辟除」。但是現代恐怖故事與電影製造的恐懼,是靠著將你我隔壁鄰居一樣的真實人物具象化而達成,甚至連我們的醫生在電影中都可能是惡棍。更重要的是,吃人魔漢尼拔、傑森和佛萊迪在電影中是不會死的,更不要說遭到辟除了。相反的,他們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到情節中。
就算在殺手不是反社會人格者的電影中,一再出現的情節公式是一開場就鮮活呈現壞人對無辜者做出一些可怕的行為,讓後續暴力報復的劇情合理化。而主角多半與受害者有某種關係,讓主角的隨後展開的私刑報復(以同樣鮮活生動的方式呈現)站得住腳。
我們的社會就這樣創造了一大盤促使一整代美國人享用後可以獲得殺戮能力的大餐。製作人、導演與演員窮盡想像力,以鉅細靡遺的方式描述無辜的男女與小孩被刺殺、槍殺、虐待或折磨。他們催生出最暴力、可怕、恐怖的電影,並因此獲得了可觀的酬勞。他們讓這類電影既暴力又有娛樂效果,同時讓(多半是)青少年觀眾享用甜點與軟性飲料,讓他們能夠結伴觀賞,男女朋友還能夠在電影院產生親密的肢體接觸。青少年觀眾因此建立起這些獎勵與看到的電影內容之間的關係。
觀眾在銀幕上出現可怕情節時閉眼或轉頭不看而被人瞧不起或羞辱,多半是群體壓力發揮作用。青少年的同儕團體對於能夠實踐好萊塢標準、也就是面對暴力不為所動、依然故我的人,通常會投以尊敬與羨慕。這種壓力實質上等於腦袋被一個心理夾具固定而無法轉動,而社會壓力又撐開他們的眼皮,使得他們無法閉上眼睛。
我在西點軍校與阿肯色州立大學講授心理學課程,談到這些電影以及上述的心理反應過程時,經常詢問學生,當電影中呈現的壞人角色以某種特別恐怖的手法殺了一位無辜角色時,觀眾的反應是什麼?學生們一成不變的答案是:「大聲叫好」。也就是說,對於這種劇情呈現的傷害本質,我們的社會處於一種否認狀態,但是,這些劇情的影響效率、製作品質的精良以及影響的範圍,其實遠超過「發條橘子」與美國政府在訓練士兵上的付出;後者的效果根本相形見絀。納魯特中校作夢也想不到,我們的社會靠著減敏感與制約方法而讓人民擁有殺人能力這件事上,可以達到這種成就。如果我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培養一整代人成為橫行無阻、不理會政府、也不會對受害人心生憐憫的殺手與殺人者,那麼,我們現在的成就就已經好到沒有再進步的空間了。
在影視出租店的恐怖片區中看到的封面,一定有露胸(往往是血跡斑斑的胸部)、挖空的眼眶,以及支解的屍體畫面。一般來說,許多出租店根本不陳列列為X級、封面比起恐怖片還比較不露骨的電影,就算有,也是放在一個專門陳列成人片的房間。相反的,恐怖片卻放在每一個孩子都看得到的地方。難道,活女人露胸是禁忌,卻可以容忍大卸八塊的露胸屍體出現在眼前?
墨索里尼與其情人當年遭到公開處決,兩人屍體並倒吊示眾。其情人的裙子因此遮住了頭,露出大腿與內褲。群眾中一位美軍士兵看不過去,上前將裙擺塞到她的雙腿間,這個動作顯示了他對死者的尊重。她或許死有餘辜,但是她死後不應該再受到這種污辱。
我們在哪裡丟掉了這種尊重死者的得體行為?我們怎麼會變得麻木不仁?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系統性的減敏感已經讓我們的社會對他人的痛苦與苦難無動於衷。我們也許覺得,八卦小報與電視節目煽情報導受害人的故事,會讓我們對他人的苦痛更加在意,但實情是,因為這些媒體年復一年地必須發掘更奇怪、聳動的新聞,以滿足胃口更大的讀者,所以這些報導的效果反而讓我們減敏感、並將這些新聞瑣碎化。
我們現在正處於減敏感的時代,受苦承痛在這個時代成為娛樂的素材、一種替代的樂趣,而不會讓我們感到不舒服。我們正在學習如何殺人,同時也在學著如何喜歡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