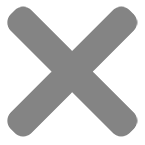一直以來,我的思考模式都蠻悲觀的,任何事情都會想到糟糕的層面,接著鑽牛角尖轉不出來。
但真正確定診斷憂鬱症,開始接受治療是在高二。治療的方式也很簡陋,平常在學校會每周一天到輔導室與輔導老師晤談,有時候學校也會找高醫(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精神科醫師幫我做治療(其實也是晤談,就是比較專業的聊天),假日再去身心科診所做追蹤,醫生會簡單問診,大約五分鐘左右(因為病人很多,無法跟我聊太久),接著開一些助眠劑、抗焦慮劑跟血清素給我吃。憂鬱症患者大腦的血清素分泌不足,因此會以藥劑的方式補充。不過這些藥物會讓我食慾缺缺,因此要強迫自己吃東西。(因為諮商蠻貴的,一小時要一兩千元台幣起跳,健保又沒有補助;看精神科有健保,因此家裡只能負擔看精神科的錢,而諮商就使用學校的資源。)
說起來有點諷刺,當時年紀小,真的不知道自己得了憂鬱症,更不知道身心科、精神科、心理諮商、精神科醫師、心理師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由於我是高雄女中醫護小天使的成員(類似急救隊的學生組織),平時會在保健中心值勤,有一次整理櫃子時,意外看到一疊由董氏基金會發行的「憂鬱症自我檢測量表」,便拿了一張來寫。寫完不得了了,每個題目我都點頭如搗蒜,真是講到心坎裡,當然憂鬱指數到達最高危險等級。
於是回家我拜託母親帶我去看精神科醫生,告訴她我有憂鬱症,需要治療。父母那一輩對精神疾患有很嚴重的偏見,記得他們曾嫌惡地說:「蔡某某(一個親戚)有憂鬱症,好可憐,怎麼會得這種病。」當我告訴她我要求診時,她只說:「妳想太多了,怎麼可能得那種病?」之後我仍舊不斷告訴她,我真的很痛苦,拜託妳讓我看醫生,我很不快樂。
母親卻說:「妳不要一直往負面想就好了嘛,快樂一點啊!」
不會有人跟自體免疫疾病的患者說:「你的細胞不要去攻擊自己健康的細胞嘛,健康一點啊!」
為什麼要叫憂鬱症患者「自己快樂一點」?
我們會憂鬱,就是因為喪失情緒調節的能力阿。
媽媽那邊講不通之後,我轉而向護士阿姨求助,由她幫我轉介輔導中心,開始晤談。後來母親才勉強同意帶我去看醫生。
事實上,這些年來,我也不斷地閱讀書籍,來了解憂鬱症,也要花很多時間跟父母解釋我的狀況。
舉例來說:我可能會因為跌倒,就會違反比例原則地崩潰大哭。一般人這時候哭泣是因為腳扭傷的疼痛,而我是心底湧現更龐大的悲傷,想著我運氣真不好,怎麼這麼可憐,為什麼受傷沒人幫我,我是不被愛的,不值得活著。這樣的情緒反應大過強烈,有違常理,常讓父母不知所措。或是,大二的時候有一堂課要寫Matlab的程式,但我怎麼聽都聽不懂,翻書也找不到答案,每天都以淚洗面,打電話跟爸媽說我要休學,甚至再次激發自殺的衝動。對於小挫折,我會相當敏感,非理性的放大悲劇程度,一旦遭遇更大的難關,我就會脫口而出:「我好想死,拜託讓我死。」
我不是說說而已,我是真的很想死,每分每秒。
但我必須讓父母知道,因為憂鬱症的關係,我特別容易悲傷,也很容易有自殺的念頭。我不是「把死當玩笑」在說,也不是不願意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只是,我真的承受不了這些風吹草動。我的父母是辛苦的,自己上班的壓力已經很大了,不能把他們的負能量傳遞給我,還要不時監控我的狀況,幫我加油打氣。這些年,他們對我說話也變得小心翼翼,怕無心的玩笑就傷害到我,也逐漸接受他們的女兒是憂鬱症患者—他們曾經鄙視的那種人。
那時候我很討厭諮商,因為我覺得「很廢」,每次花一個小時,輔導老師就坐在那邊聽我說話,跟重複我的話而已(所謂同理、傾聽),什麼實質的問題都沒解決。我就是家庭不和諧,爸媽不關心我;我就是跟同學處不好,沒人要跟我當朋友;我就是成績很爛,考不上大學;我的人生一蹋糊塗,未來也是悲劇性的延伸。妳為什麼不做點實質一點的事,只坐在那邊聽我說話,不時點點頭而已?
有一次去看診時,身心診所的精神科醫師說:「妳一定要找到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才能改善妳的狀況,不然一直吃藥也不是辦法。」
什麼是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可分為下列四類:情感性支持、實質性支持、知識性支持和評價性支持。但白話一點來說,就是得建立一個社交網絡,在你遇到困難的時候,能幫助你。舉個例子好了,當你微積分快被當掉的時候,你的室友寫了一張加油紙條藏在課本裡,是情感支持;當你的同學半夜還陪你解練習題,是實質支持;當你的導師提供給你一些自學網站,並告訴你,有努力就好了,重修一次不會丟臉,這是知識性支持;當你的學長告訴你,其實每年重修的人有一百多個,你及格了表示你很厲害,但你被當了也不過是正常人而已,不需要沮喪,這是評價性支持。不論是心理層面的,或是實質面的幫助,都是人在群體社會中能夠生存所具備的要素。
但是,我沒有朋友,一個都沒有,跟父母的關係又很疏遠。我要去哪找到社會支持?
我仍舊孤單了很多年,雖然斷斷續續有認識對我友善的同儕,但都是淡如水的狀態,不是能拜託他幫忙買早餐,或是深夜談心的關係。也許,她們願意當我的朋友的,只是沒有契機能更深入交往,而我對別人的心牆又築的很厚,始終維持著表面的關係。而我的社交網絡,其實也是這幾兩三年才建立起來的,從真正交到第一個好朋友開始,我才知道「原來什麼是朋友」、「朋友會一起做那些事」,他們教會我怎麼跟別人互動,讓我有機會得到更多朋友,也逐漸聯繫上以前的同學,其中某些人也成為我現在重要的友人。不過關於這個朋友的故事,後面的章節再詳細述說。
那時候,高中老師很多都是雄女的校友,很喜歡在課堂上說:「人一生中最好的朋友,都是高中同學,所以妳們要好好珍惜身邊的人。」我聽完哀慟不已,我高中一個朋友都沒有,代表我這輩子再也找不到朋友了?
也許諮商能幫助你舒緩一些痛苦的感受,但人生之路很漫長,要能好好走下去,還是得建立一個「人際安全網」,也就是社會支持。就像大樓內的天井,通常會掛上一張白色的麻繩網,防止有人掉下去那樣。人際安全網是為了在你人生遭遇變故時,能夠及時網住你,讓你不會持續下墜的保險。
但最難的是,第一個朋友,要怎麼得到?
憂鬱症治療困難重重的原因在於,通常患者的社交技能很差,情緒控管也失能,因此跟別人相處時常常會惹怒他人,所以沒人想當他們的朋友。但沒有朋友,也就是沒有社會支持,會加重憂鬱的情況。於是,常常這樣惡性循環多時,許多患者撐不過去就自殺身亡了。
可是,大家不會強迫小兒麻痺患者去跑大隊接力,在他速度很慢,讓班上失去名次的時候,怪罪他。那為什麼,當憂鬱症患者無法表現出活潑、開心,甚至社交應對上不適切時,卻沒有人諒解?只因為身體的疾患是外顯的,容易被看見,以及非患者自願的。但多數人,會把憂鬱症解讀成性格上的缺陷,看似他們咎由自取(患者自己不願意樂觀一點的)。
能不能,給憂鬱症患者多一點包容,多一次機會?
因為太寂寞了。寫日記成了我生命最後一條防禦線。當我情緒逼近潰堤邊緣時,我一定要寫日記。我隨身都要攜帶紙筆,無時無刻的寫。有心事無人可吐露,於是我在日記上跟自己對話。寫下今天發生的事,自己的心情如何,誰對我說了什麼,我的感受是什麼,最近看了什麼書、電影,得到什麼啟發。最後,再寫下最近的目標,跟一些鼓勵自己的話,像是:「閔筑加油,妳很棒,這次作文分數比上次高兩分喔,老師的評語寫有小說家的潛力喔!妳現在還很年輕,做不好沒關係,之後還有十年二十年可以努力,之後會更進步的,不要放棄喔!」
因為生命裡幸運的時刻太過稀少,一定要努力地刻劃在日記裡,提醒自己曾經幸福過。即便,那僅有幾秒的時間。
情緒低落的時候,我不敢讓別人知道我有憂鬱症,因為社會對憂鬱症仍有偏見,我不想接受異樣的眼光,也不願他人因此給我奇怪的特別待遇。然而,當情況好轉的時候,依舊無法坦然地讓別人知道我有憂鬱症的病史,因為我不確定他們能否接受這樣的我。
大一大二的時候,我已經很會偽裝,即便心裡難受,還是會繃著一張笑臉面對別人,回到房間裡再把自己關起來放聲大哭。當我偽裝的越好,面具收藏的越多,我越不敢說出真相,因為我怕別人願意跟我當朋友,是因為「我扮演的角色」,而不是真正的我。在這個極度崇尚樂觀與外向的社會,想要生存,得學會成為樂觀開朗的樣子,畢竟,沒有人想無時無刻被負能量轟炸。努力一點,可以辦到,但很耗費心理能量。總是有那麼幾天,感覺好疲憊,不想再裝了,想做回原本的自己—那個憂鬱到極點的自己,不過我真的好怕,是不是又會失去所有朋友,變成一個人了?
甚至到現在,我終於能夠泰然自若地說出:「我有憂鬱症病史,接受治療很多年了,現在算是復原期,但哪天會復發也不知道。」但我還是會怕,是不是有人會覺得,這些故事都是假的,都是我杜撰出來的。
有一次接受治療時,高醫的精神科醫師告訴我:「我高中唸北一女,高一也是憂鬱症,成績很差,但我高三的時候成績有救起來。後來,就像妳看到的,成為精神科醫師。很多時候,我都會問『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我生病?』可是後來我會這麼想,也許上帝現在給妳這個考驗,是為了讓妳日後能幫助跟妳受過一樣苦的人。因為,妳能夠真正的了解他們。」
是的,有憂鬱症經驗,以及接受過心理學專業訓練,加上有能力書寫成章的人,不多了。 這是種責任感吧!想幫助那些仍在與憂鬱症搏鬥,或是情緒困擾的人,所以,我正在寫這本書。
補充說明: 憂鬱症最廣泛的定義是:兩周以上持續的心情低落,且自身無能力調節情緒,造成生活上的困擾。如果您不確定自己是難過還是有憂鬱症的狀況,可以先上填寫董氏基金會的線上自我檢測量表,若發現有罹病可能,請盡快就醫。
 憂鬱症與憂鬱情緒的差異,引用自《圖解憂鬱症完全指南》原水出版
憂鬱症與憂鬱情緒的差異,引用自《圖解憂鬱症完全指南》原水出版
- 董氏基金會線上憂鬱量表:https://www.jtf.org.tw/psyche/melancholia/overblue.asp
Take home messages :
- 若發現自己或朋友有罹患憂鬱症的可能,可以先做自我檢測量表,並尋求專業協助(看身心科、衛生局的諮商服務、打1980張老師或1995生命線線)
- 憂鬱症患者的社交能力與情緒調節較差,請大家多多包容
- 寫日記(書寫)是一種自我療癒的方式
- 憂鬱症初期很難察覺,經常出現失眠、食慾降低等生理特徵,因此一開始容易被誤判
文末的murmur:
事實上,諮商的治療是非常慎重的醫療行為,治療師也需要經過多年的培訓才能勝任這個工作。上面文章我會說「諮商很廢」,是因為每個人對於諮商的效果反應不同,另外是我除了情緒調節的困擾外,家庭、人際及學業等各方面的問題都是束縛我的問題,那當下真的過得很痛苦才會那麼說。所以,看完本文,請不要隨意曲解文意,貶低諮商師與心理師的專業。
本篇為《離開病房之後》連載第二回,若想瞭解更多故事可以點前兩回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