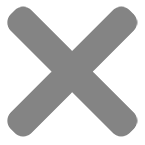會影響司法判決的,除了法官是誰之外,還有她是怎麼想的。如同前文所討論的,我們的決定會同時受到兩件事的影響—快速而自動反應的直覺,和比較慢、可受控制的考慮。你可能會認為法官—由於他工作的本質和所受的訓練—一定是經過審慎的推論之後才作出決定,但其實法官經常—甚至有些研究者認為主要是—根據直覺在作決定的。就和我們其他人一樣,當法官必須作決定時—不論是決定要不要把證據呈給陪審團看,或是將一個人判刑—他們也都會在腦中走捷徑。
有時候,這些腦中自動冒出來的經驗法則其實滿有用的。如果一個法官不確定是否該駁回一個異議,他可能會試著回想自己以前和某位律師的互動—他的異議看起來都很不必要,但是可以激怒對造的律師。這可以幫他作出正確的決定。不幸的是,這些直覺的過程也可能造成系統上的錯誤—如果都只根據不相關的線索和值得懷疑的連結的話。
想想所謂的「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最初的一個數值(例如我問你電話號碼的最末兩碼是多少)最後會形成評估的結果(例如你認為這瓶紅酒價值多少)。在一九七○年代中期之前,研究者就發現,只要拋出一個數字,人們對於某件事的判斷(例如非洲國家在聯合國會員國中的比例)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不過,如果因此就認為,這也會影響一位有經驗的法官對於真正重要的事所作的決定(例如一位車禍被害者在失去右手之後,應該要得到多少賠償金,或是一個強暴犯或慣竊應該被判刑多少年),似乎還是過於跳躍。然而,當研究者真的對法官提出這些問題時,他們發現有明顯的證據證明,錨定效應確實存在。當法官們被要求對一個假設的被告判刑時,他們很明顯地會受到不相干的因素影響,例如記者在法庭休會時,透過電話所作的民意調查中提到的數字(「您認為這個案件中的被告如果被判刑,應該超過或低於三年?」),或是檢察官隨機地對法官建議的求刑年限。令人震驚的是,就算是擲骰子得到的結果,也會影響到法官正式宣告的判刑。
還有另一點令人驚訝的是:這個研究顯示專門知識和經驗並沒有特別的幫助。如果受試者是刑法專家,或是曾經處理過與假設問題類似的案子,也一樣會受到不相關的數字影響,就和沒有相關背景的法律專業人士沒什麼兩樣。雖然也有其他研究認為,專門知識—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讓法官避掉外行人容易有的認知錯誤,但是在這個研究中,專門知識的功能似乎只有讓法官對於他們的判決更有自信。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其實原因也不是個祕密:法官常常必須在充滿不確定的情況下為一個問題下決定。任何人都無法確定是否應該准許交保、被告的照片是否會引起不公平的偏見,或是什麼時候應該宣告審判無效。法官要回答這類問題時,能依靠的證據通常是彼此對立的,所以也沒什麼幫助—因為制度中的兩造本來就是對立的,其中的檢察官和被告必須分別提出支持他們的論點。因此,如果一些不實的訊號提供了解決之道,法官便很容易受到影響。而且法律的規定也讓法官通常無法達到理想的目標。
例如:法律上要求法官不可以考慮會引起偏見和不相關的事實(像是被告曾經在五年前因為搶奪錢包而被逮捕)。雖然這看起來是要讓法官只考慮被告在本件中的竊盜罪,不要讓其他的事實幫助證明他是有罪的。不過,有兩組不同的研究者都發現:當現實生活中的法官要決定一個假設性的案件時,他們通常無法排除這些資訊的影響—就算有人明確地提醒他們:他們被告知的這些事實不應該被列入考慮。

性別、種族、階級和其他許多因素也都有類似的軌跡。法官們都很清楚不應該讓這些因素影響判決的作成;其實,他們還常指示陪審員在評價證人、被告和辯護人時,不可以受到這些差異的影響。不過,法官也只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在這個社會中,這些因素就是會帶來許多聯想,例如對婦女的刻板印象就是相夫教子,或是對於變性人的想法。人不會因為穿上了法袍,就輕易的擺脫一個人的成見。
如果法官一貫的持有偏見,那麼,他們是不是會一貫的保持相同的偏見呢?有一組研究者對於這個問題感到好奇,於是他們決定看看,法官在一整天中是如何作決定的?調查者把重點放在兩個以色列的假釋裁決委員會裡,八位經驗豐富的法官身上。
整體來說,在受刑人所提出的申請中,有百分之六十四.二遭到這八位法官的拒絕。但這不是這些研究者感興趣的部分:他們想要知道在一天中的不同時刻,這些法官會不會作出不同的決定。如果假釋案在一早就提給委員會,或是在午休時間剛過時提出,結果會有不同嗎?如果法官只是裁判,就不應該會有影響:好球就是好球,和太陽在哪裡應該沒有關係。不過這些現實世界的法官又是如何呢?
針對超過一千件裁定所作的分析發現,法官在一天的上班時間剛開始的時候,和兩次用餐的休息時間過後,特別容易通過受刑人的假釋申請—有約百分之六十五的申請會獲得同意—相較於此,如果是一天的尾聲,或是休息時間之前,通過的件數幾乎是零。除此之外,像是犯罪的嚴重性、受刑人已經服刑的時間—這些才是真正應該影響法官決定的因素—卻反而對於裁定結果沒有什麼影響。一天裡的時刻似乎才是件重要的事。
怎麼會這樣呢?
進行研究的人假設,在一天要結束之前,法官在精神上會感到耗盡心力,讓他們選擇在認知上比較容易的作法,而且傾向於堅守現狀:駁回假釋申請。一直作決定會耗盡我們的精神和腦力,為了克服這種疲勞,我們可能需要休息,或是更多的葡萄糖—從字面上來說,就是動腦所需要的食糧。
最讓人感到憂心的,是這並不是什麼實驗室裡所作的實驗。以色列有約百分之四十的假釋申請,都是由研究中所涉及的兩個假釋裁決委員會處理的。而法官對於他們偏見的本質或程度毫無所覺。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精神上的疲憊會帶來如此大的危險:通常你一點都不覺得累,所以也不覺得自己的判斷會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
當然,法官會想要保持一致。而最近一個令人沮喪的研究結果顯示:這種願望其實反而更會造成我們的偏見。身為一個教授,其實我每個學期在打成績時,都會面臨這個問題。例如在我的刑法課上,我只能給(頂多)百分之二十的學生A或A-。雖然從統計上來說,在一個八十人的班級裡,我也可能在前五份考卷中就改到三個A,但是我預期五份中只會有一個A,這個預期可能會逼使我改變評分標準(在這個例子中,是讓我對於前面答得好的考卷變得比較嚴格)。研究者把這種現象叫作「狹窄性取景」(narrow bracketing):必須要接連作出判斷的人,會把要判斷的對象分成小組,對每一個小組作孤立的考量(例如:在午餐前改完的所有考卷,或是在一天之內看完的所有案件),並避免讓結果與預期的分配方式差太多。這個研究顯示:雖然法官只要從申請名單中准許五名受刑人的假釋申請就好,不過如果先連續同意四名的申請之後,法官就不太可能繼續同意第五名的申請,只因為這樣會不符合他所預設的狀況(也就是每三人中,只應該同意兩個人的假釋申請)。
法官對於某個案件的判決會影響他的下一個判決,或是這個案件在一天中的什麼時間被提出,會影響到它的結果,這都和我們對於公平的司法體系的想像完全不符。我們必須繼續努力,更進一步地了解會影響司法判決的力量。如同法理論家和上訴法院法官傑羅姆.弗蘭克(Jerome Frank)早在一九三○年所寫的:「如果法律包括法官的決定,而那些決定是根據法官的直覺作成的,那麼,法官的直覺從何而來,就是司法程序中的關鍵了。什麼形成了法官的直覺,什麼就形成了法律。」
所以,法官並不像是羅伯茲首席大法官所說的那般客觀、中立和公正無私。其實,他們也不是真的能夠做到裁判或判決者的角色。

當社會學家在研究司法判決的過程時,也有其他學者投入研究裁判的偏見。兩者的發現有驚人的類似:雖然在不同的運動中,裁判都想要表現得中立和客觀,但是最後還是會作出扭曲的裁判,或是在指揮比賽時出現不公。例如:網球賽事委員會容易受到知覺偏誤(perceptual bias)的左右,就很類似於法官和陪審員會受到照相機視角的影響。裁判看到球落地的點,會隨著球的移動方向而轉變,所以他比較容易把界內的球判成出界(把界外球判成界內的情形相對而言比較少)。就和法官一樣,裁判也會被一些不相關的因素左右。如果裁判是白人,白人打者的好球帶就比黑人打者小;在跆拳道比賽中,穿紅衣服的參賽者會比穿藍衣服的參賽者得到更多點數;如果兩個足球選手相撞,高的那個比較容易被認為犯規。除此之外,就像法官會覺得應該依分配拒絕某些假釋申請,於是在潛意識中改變了他們的決定,籃球裁判也會平衡兩隊的犯規數,棒球裁判則會在兩好球之後縮小好球帶,並在三壞球之後放寬好球帶。而且,就像法官一樣,裁判也不可能完全不理會觀眾的聲音:在很多運動中都可以看到裁判對主場球隊的偏見根深蒂固,觀眾的數量越多,偏袒地主隊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們許多人都希望法官只是裁判的角色,但或許我們真正想要的,是機器人法官—而且它的程式不是由人類所設定的。如果是血肉之軀的裁判員,他腦中的硬體就一定和我們其他人一樣受到限制—電路只能夠符合更新世(Pleistocene)的需要,處理器太慢無法同步,儲存的硬碟容量也不夠。

以上內容摘錄自《不公平的審判》(臉譜出版)
本書就像精彩的犯罪推理短篇小說集——但書中情節卻都是真人真事。針對司法體制,作者提出了我們最在乎的問題:「正義究竟該如何達成?」藉著對證人記憶、犯罪心理等的深入剖析,作者也揭露了人類心與腦的運作實際上如何恆常地偏離認知的常軌,而我們又可根據最新科學進展,如何有效修正偏失的司法準星。
進一步暸解本書內容:http://ppt.cc/Syc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