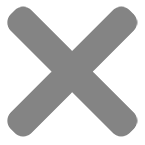強納森,民國76年(台灣解嚴)出生。國小時行為問題嚴重卻因小聰明從未被發現;舉凡虐狗、縱火、破壞公物、偷竊、欺負同學等,無惡不作。國小六年級第一次寫下遺書,國中和高中均為輔導室的常客;國中已有自殘傾向,曾在腿上刻下喜歡的人姓名,但當時沒有人建議過我要去求醫(可能也跟我小心隱瞞有關)。
20歲時首次看精神科是由家醫科轉過去的,當時身體嚴重失調,家醫科的醫生卻小心翼翼的「建議」我去隔壁精神科掛號。在此沒多久後嚴重發病,歷經多次的自殺、洗胃、休學、服藥過量…最後花費七年念完大學。過程中由於藥物不見效,兩年後便自行停藥;當時由於有穩定工作,停藥後也還過得去。
後來為了申請美國電影研究所而辭職,壓力驟升下又回精神科掛號,這才被確診為躁鬱症第二型─也就是雖然不曾躁症病發,但只有躁鬱症的藥對我有效。第一次吃下鋰鹽後終於嘗到當「正常人」的滋味,目前已來到國外學習電影,也依然靠藥物有效控制。此外從畢業後就開始自費諮商,迄今已滿三年,也算是我病情漸趨穩定的因素之一。
我的第一次住院在剛發病的20歲出頭,當時其實算是被強制,加上住院過程遭到性騷擾醫院卻完全無處理打算,「住院」因此對我留下巨大陰影。此後無論醫生再怎麼威逼利誘我也不肯住院,直到我在多年的諮商後終於認知到有時候,我就是必須靠別人的幫助才有辦法控制自己,才決定再給住院一次機會,也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一、引言
我不算甚麼嚴重的病人,住院也只住過兩次。因此,我只能由自身經驗出發來書寫我看到的精神病院。此外,我個人的記憶和認知都可能有偏誤之處,因此我寫下的一切也許有些部分只是我的誤讀。但無論如何,我還是想寫下這些觀察,記錄自己在病院中度過的時光。
二、誰需要住院?
精神病院在西醫邏輯下的目的,是保護其內的精神病患免於「破壞秩序」─如果做出自傷/自殺、傷/殺人 (但遇到傷/殺人者,精神疾病可能並非首要被考慮的面向),或有幻視聽 (對「不存在的事物」做出反應)、妄想 (懷疑有人要加害自己或其他扭曲現實的認知)等症狀,就被視為是破壞了社會常規。在此,精神疾病醫療系統將會介入,將這些患者收進精神病院;這不僅是為了保護患者自己,也是為了將患者與社會大眾隔離開來,讓社會得以依循其既定邏輯運轉。
那麼,住院的標準到底在哪裡?難道要等患者傷人/殺人了,才能送醫治療?事實上,精神病患真正會傷/殺人的只在少數,而且在謀殺犯當中,精神病患的比例其實也很低。通常會住院的患者都是自願的,他們可能是為了調整藥物 (失眠等症狀)、有自殺/傷或殺/傷人意念 (未見得有行動,只要意念強烈即可住院)、幻視聽、妄想 (但前述二者比較可能是被家人送去的)。住院不僅是為了杜絕可能的危險行為,也是為了更有效率的調整藥物,以利控制病情。
我自己的兩次住院,都是因為自殺/傷意念及行為,因此我也會以這類患者的角度撰寫本文。
三、入院:強制與自願
台灣的法規面對精神疾病患者已是數一數二的重視人權,也就是說即便一個人有了自殺/傷或傷人的事實,都不見得能保證強制住院。看待這件事情的面向不只一種;從某些被我們判定「腦袋不清楚」的患者家屬的角度,就會希望標準越低越好,以利他們強制自己的親人住院,盡到治療 (但某些時候也許只是隔離)的目的。
然而我們退一步想,到底何謂「腦袋不清楚」?是聽到不存在的聲音,看見不存在的東西,還是揚言要殺人、自殺,甚至已有傷害自己的舉動 (傷害他人是法律管轄範疇,在此不討論)?事實上,這裡每一項都並非剝奪一個人自由的好理由;然而當我們將一個人判定為「腦袋不清楚」時,我們實際上便已是剝奪了這個人被視為行為人的基本權利。
法律所選擇的「視人為 (行為) 人」的界線,不但影響大多數位於常態分佈正常範圍中的人,也同時影響曲線兩端的人─姑且分類為極有病識感和極無病識感。對於極無病識感那端的人,家屬很容易認為應該放寬強制標準,然而由於所有人都適用於同一套標準,這也將意味著有病識感的人更容易遭到強制,結果便是我們用法律踐踏其尊嚴,卻找不出一個好理由 (為了讓沒病識感的人更容易就醫?這是不相干的兩件事)。而且,這還只是假設無病識感的人不會因尊嚴遭到剝奪而痛苦,但誰又能保證實情如此?
總之,事情就是這樣了。將標準放寬,無病識感者較可能得到所需的醫療,代價卻是有病識感者的尊嚴遭到剝奪 (並有可能近一步造成延誤就醫);讓標準變嚴,有病識感者在尋求醫療資源時較不須擔心失去自由,卻可能造成無病識感者就醫的延誤。這條線的拉扯,最終將會顯現我們社會所重視的價值。
說了那麼多關於強制住院的內容,但實務上除非病人非常劇烈反抗,否則也多半是自己簽同意書入院。我的兩次住院都自願簽了同意書,但第一次簽下去前卻遭受威脅說我若不願簽,就可能要強制住院。我是在多年以後才學到,他們要強制你還沒那麼容易。
四、入院:儀式
第一道儀式在上一節末尾已經提及,就是簽署一大串的同意書,把你的「自由」簽給醫生和護士。這裡對「自由」加引號,是因為大部分醫院剝奪了患者的行動自由,然而有些醫院甚至連身體自主權都不留給患者。我曾見過一位對於行動受限有所不滿的病友稍微大聲地對也同樣不耐煩的護士抱怨了幾句,卻遭到護士強制對他打鎮定劑;他雖不願配合,但看在被幾位保全壓制住的份上,也只能半推半就地接受。某種程度上,這與上一節所說的強制就醫邏輯相同─我們假設患者並非和我們平等的高智慧生物,卻無法否認這樣的假設只是一種圖方便的手段。不過,不同於上一節中描述的那些強制住院患者,這位遭施打鎮定劑的病人是自己將自己的自由簽了出去,因此法律再也無法保護他的尊嚴。
第二個儀式:去個人化,以安檢為名。安檢也就是安全檢查,你的所屬物品一項項被倒出來仔細檢查過,確認裏頭沒有違禁品 (鑰匙和雨傘不行、手機等電子儀器一律禁用、塑膠袋一定要剪破一個洞、毛巾和浴巾禁止,只能用方巾、褲子有鬆緊帶的要抽出來沒收、竹筷和叉子不行、耳機有些醫院全面禁止,有些必須寄放在護理站,需要時可以「借用」、藥物不行、菸酒當然別提、而洗衣粉需要寄放)。檢查完後,東西又被丟回行囊,我便順利成為一個無論對自己或他人都不具 (表面上) 威脅的人,也就是「病友」。前面寫道表面上不具威脅,是因為病房實際上還是有許多安全漏洞,真要自傷或傷人總還能想出各種創意十足的方式,如折彎電話卡取出 (銳利的) IC 晶片、利用被單、被套等 (請勿學習),且病友之間這類的資訊流通也十分迅速。
最後一道儀式,是重新賦予我一個專屬的院內身分,由病人手環開始。每位病友都會戴上一個防水手環,這就好像牛耳上的烙印,在放藥等活動時方便管理者認出牛隻/病友。接著,每位病友會得到一個床位和在護理站的一個置物櫃,裡頭收納一些略有危險性、不適合放在床位、容易弄丟,或需控管使用的物品。最後,病友會得到一整張的姓名貼紙,貼在個人物品上以避免搞混。待這一切結束而我也回到自己的床位上時,我就終於完成了我的入院儀式。
五、生活:公共空間與隱私
每位病友通過入院儀式後,就必須面對兩種不同的空間─私人的和公共的。通常每間病房裡都會有數張床位,這即是私人空間─雖然還是帶有公共色彩,因為病床之間難有隱私,即使是在病房空間大、甚至還有拉動式布簾分隔病床的 B 院也一樣。不過相較於更開放的空間 (交誼廳、護理站),病房仍可說是提供了些許隱私。整體而言,病房能否讓病友保有隱私,仍攸關病房的空間設計。
許多病房設計成走廊形式,走廊通到每一間房間,而交誼廳則設置在他處 (走廊末端或中間)。這樣的設計讓病友與家屬及醫護人員間的對話較不易被其他病友聽見。相反的,如果所有病房都通到交誼廳,那麼新聞散播的速度根本如野火一般,剎那間就燒到所有人。隱私為何重要?它是否是一個成年行為人的基本權利姑且不談,醫病間本應有的保密條款,也會被缺乏隱私的空間設計破壞殆盡,而這多少也反映了設計者心目中的醫療邏輯。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空間設計所導致的物理上的接近,多多少少也造成病友間情緒狀態的接近。比如我住在 B 院時,同房有位病友入院第一天早上就痛哭不止,除了被嚇醒的驚愕外還必須費點力氣安慰該病友,導致我自己的情緒也受到影響。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實際上病房還有各式各樣的雞飛狗跳,有時為了避免太被影響,甚至必須離開自己的床位到「外面」休息一下。「公」與「私」的概念有些模糊,這無疑是住院生活的特色之一。
六、生活:一日作息
病院的一天由散步開始。有許多病友沿著走廊或其他公共區域散步,這幾乎算是精神病院的象徵之一了。由於大多數精神病院都早早 (晚上九點至九點半間) 熄燈,因此早上起得也早。此外,由於大多數住院環境會讓病友缺乏活動,因此許多病友會為了保持健康/刺激消化/排解無聊,繞著活動空間來回走動。一些症狀較為嚴重的病友即使全身僵硬、對著空氣說話,都還依舊保持著這個習慣;反倒是我這個「有太多事可以做的人」,往往懶得驅策自己走個幾圈。
在散步後,接下來的作息時間幾乎均由吃飯做為區分點;每餐飯後都是給藥時間,而餐與餐之間就是上課與玩耍時間,必須自己找事情打發掉。由於手機等電子產品均被沒收,住院生活其實非常無聊,因為平常無聊時可以做的事 (打電動、滑臉書等) 都無法企及。至於看書雖然可以排解無聊,但許多人跟我一樣,在狀況差 (剛入院) 時,是無法集中注意力閱讀的。所以,最後一道防線便成了病院均會提供的博奕遊戲,讓病友在殺時間之餘維持社交,不至於無聊出病來。
睡前該做的還有洗澡,時間每個人不一定─我通常喜歡下午洗,不過常常碰到塞車,顯然許多人跟我喜好一樣。因為在熄燈後 (九點))就不能再洗澡,所以下午先洗好就不會縮減到晚上的玩樂時間。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病院唯一真正有隱私的地方就是浴廁,而醫院為了防止病友在裡面自我傷害,所有的水龍頭都是連在牆壁上、不接水管的。最後,在吃完睡前藥後,就是熄燈和關電視的時間。夜裡仍會有護理師固定巡房,加上監視器的嚴密控管,能將所有患者的睡眠狀況詳實紀錄,而明天,又將是與今日相去無幾的全新的一天。
七、生活:上課與娛樂
所謂的上課是指職能治療。對於第一次住院、失能不太嚴重的人來說,多少會覺得職能治療這種課程有些莫名其妙,不明就裡的長在病院的固定行程裡,也沒有人向你說明它們的目的。不過,多住幾次、遇過許多不同狀態的病友後,就會了解有些人的確需要這種課程幫他們復健,比方說因嚴重憂鬱而反應遲緩的病友,或者因躁鬱症而無法專注的人。職能治療的活動包括書法、畫圖、運動、唱歌等,由幾位治療師帶領病友進行活動。除了急性病房外,日間病房也有職能治療活動;有些病友偶爾會離開急性病房參與特殊的職能治療課程。
至於娛樂,也就是上一節中提到「自己找事」的「事」。精神病院的玩樂頗為精彩,院方幾乎都會提供各種博弈器材,如撲克牌、各種棋類,還有最重要的─麻將。我的暗棋和象棋都是在精神病院學的,麻將則是牌技精進─畢竟除了精神病院,還有哪裡能夠讓你沒日沒夜地打免費 (不賭錢) 麻將呢?除此之外打發時間的利器,大概非卡拉 OK 莫屬了。出乎意料的,點歌本裡竟然有許多我所熟悉的歌,我想那大概表示我不再年輕了吧?有一次大家在唱歌時,隔壁一位妹妹問我歌本裡有沒有周杰倫的「稻香」,我答那麼新應該沒有吧?但結果證明它一點也不新,而且完全就有。結果那位妹妹除了「稻香」,還唱了許多首我聽也沒聽過的歌,當下感覺真是五味雜陳。
八、人際:交友
在精神病院的交友很簡單 (至少我覺得比外面簡單)─你只要多去交誼廳走動 (不要一直待在床位上) 就可以了。我在清醒 (入院前多吞了幾顆安眠藥,整個人呈現半昏迷狀態) 之後第二天,就向護理站借了跳棋,原先只是想拿到交誼廳自己和自己玩,沒想到有人一看到就說想一起下,也就這麼開啟了我的第一條人脈。隨著玩遊戲的時數增長,以及有了認識的朋友壯膽,要再認識其他人就再非難事。
至於病友間除了一起玩耍,又都聊些什麼事情呢?如果你對熟悉的朋友說「我要去住精神病院」,對方第一個反應十之八九是「為什麼」吧?其實病友之間也是一樣的。「你為什麼進來」和「你的病」,是僅次於你的臉和姓名 (姓名甚至有時被擺在後面),第一條能讓人記住你的資訊。不過,每位病友管理身分的方式不同,並非所有人都願意談自己的病,這時對於這個人的印象大概就是「臉─姓名─不肯說」了。然而,即使對方不說,在病院這樣缺乏隱私的空間,大家多少會捕捉到一點邊邊角角,互相比對後拿出來亂下診斷也早非新鮮事。除了單純的不肯說外,還有一類是沒有病識感,認為自己被關起來莫名其妙的。這類人頂多可以告訴你他進來的詳細經過,卻無法告訴你原因。我就有位和我交情不錯的病友,從我入院到出院,從來沒有搞懂他為何住院。最後,當然也有人是特愛談論自己的病/藥物的。這類人逢人就問「你吃什麼藥?」但其實他也不見得很想知道,只是不斷對人重複他的傷心事。
隨著病而來的話題,便是面對病的態度。精神病院裡似乎每一個人都在摸索如何和自己的疾病和平共處,即便是那些嘴巴上說得好像已經坦然接受的人也一樣。當人們談論著自己的病時,話語中時常洋溢著一股焦慮─那或許是尋找與疾病相處之道的慌張、對自己因病而逝去的時光的緬懷,或者仍未看清自己問題的盲目。最後你會發現,那些實際上最能接受自己疾病的人,總是笑著數算過去的掙扎,因為他們已經抵達一個全新的地方。
除了身分之外,病友間第二常談論的便是自身處境,也就是「住院」的狀態。「想要出去」、「出去後要做什麼」,幾乎是最常浮現的話題。不過,多年前住過 A 院的我驚訝的發現 B 院有些病友「根本不想出院」。這些人的理由多半是喜歡受照顧和關注的感覺,或有保險可領、不用上班。保險的話題往往又延伸到重大傷病卡和殘障手冊,這便讓我想起曾詢問醫生重大傷病卡該如何申請,結果醫生的回答是1. 現在只有思覺失調症申請得到 2. 這不應是努力的目標。可是,那個領有該卡的病友「只是」躁鬱症,差別只在他是十幾年前申請的;而且,說不想工作的也是同一個人。此外,我在病院也看過思覺失調,但調適得不錯,可以工作也並未失能的病友 (實際上,在外面也看過)。
總之,為何並非以「失能」來全面性考量病友的處境,而要用生物徵狀來衡量一個人是否需要某些資源,我實在完全無法明白。一個很有錢、不必工作的思覺失調患者,和一個幾乎無法養活自己的憂鬱症患者,誰比較嚴重、誰比較需要社會資源,這難道又能仰賴生理症狀做為判準?的確,不該將拿到手冊做為目標,但也許我們該思考的是,國家所劃定的線到底嘉惠了誰,而資源又是否落入真正需要它的人手上。
最後,病友間的熱門話題當然也包括那些病院內的特權─比如持有電話卡的權利、外出的時數、外出是否需要人陪等等。有趣的是,在這些天南地北的話題之中,我們非常少談及自己在外面世界的生活。
九、人際:護理師與護理站
第一線照顧病友的不是醫師,而是護理師。護理師的業務簡直包山包海─從給藥、每天測量身體數值、保管違禁品、開關置物櫃、監測病友吃飯及如廁狀況、保管及登記博弈用具、定時點名安檢、處理緊急狀況等林林總總外,醫院還會將病友分配給護理師,而護理師每天會找時間關心自己所照顧的病友。正因病友和護理師是如此親近,最容易和病友起衝突的也非護理師莫屬了。這些衝突與院內生活的各個部分綁在一塊,是一個病友由菜鳥變成老鳥的過程中,多少都會經歷的羞辱。
比方說,成為老鳥之後你會知道有上課的時段不能借用博弈用品,以及朋友探病時如果沒帶陪病證,就只能隔著大門相望 (而且還要警衛特別通融),否則你只得接受友人來訪而你卻不知對方是誰。這些眉眉角角的小細節,都足夠讓你跟護理師起衝突,而結果很可能只是你自己情緒失控而遭到公開羞辱。只有在很少見的狀況下,才會有護理師願意花時間說服你接受一些不太合理 (只是為了管理方便,卻不把患者視為行為人) 的規定,其餘大部份時間你都必需自行吞下那些屈辱,或找同仇敵愾的病友抱怨一番(這種人不難找,因為護理師和病友間的衝突十分常見)。而如果你已是老老鳥 (住院多次),那情況又更顯不同了;你借麻將時甚至不必蒐集四人簽名,你請假外出不需有人陪伴,醫護人員也比較願意把你「當人看」。
談完護理師,該來談談護理站。護理站是護理師處理業務的主要場所,可以看做是一個熱鬧的驛站;迎接新的旅人、提供服務給留宿者,也送走踏上歸途的旅客。不過,公共電話和在某些醫院被保管的電話卡,倒是揭露了護理站的真正面貌─它是一個訊息控管中心,資訊無論出或入都得由它把關。我就時常在於護理站打公共電話時小心翼翼、篩選訊息,避免在這熱絡往來的場所洩漏不想別人知道的祕密。故此,護理師與護理站共同擔任控管者的角色,無疑是整間病院的運作中樞。
十、人際:醫病關係
相較於護理師,病友能見到醫師的頻率低了很多,不過實際次數和時間仍是依醫院而定。A 院整間病房只有一位醫師,醫師並沒有太多時間分給每位病友。B 院則是主治醫師和住院醫師幾乎每天會查房一次,而且每位病友都有專屬的社工師會介入了解狀況。在 B 院,如果說每天的生活都是為了等醫生巡房也不為過,因為只有醫生巡房時才會和你討論生活和情緒狀況,以及如何因應這些狀況調整藥物,好讓住院的進度有所進展。
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在台灣,精神科醫生的職責是「開藥」,因此你告訴他的心情都是他拿來分析藥物效用的資訊。所以,不用太期待醫生全都善解人意、富同理心,且會花很多時間與你會談 (當然,你的時間應該還是比起在門診時更充裕)。在病院,醫師的主要目的是調整你的藥物,讓你達到穩定狀態,因此從藥物出發去和他談話也許是最好的。比方說,與其只講「我昨天很想死」,可以說「我昨天傍晚左右開始想死,是不是早上的藥退了?」當然,要做到必須仰賴練習,但這樣的表達確實有助於讓你和醫師間的溝通更有效率,也能幫助醫生更快找出用藥上的平衡。
十一、 人際:性邀約
這的確是住院生活中較為出乎意料的一部份,但我間隔七年的兩次住院都遇上了,因此我想這應該不算少見。住院的整體環境是一個共同生活的環境,且由於一天 24 小時都關在同一個空間不能離開,無形之中人與人的距離就更近了。儘管男女會分住不同房間,但通常這些病房也都通到同一個空間,所以要將男女完全隔開是不可能的。
雖然並未明定,但男女之間的性交在精神病院是絕對禁止的。在這點上,病院有點像是男女混和的寄宿學校,只不過寄宿學校可能還更有隱私。多數精神病院真正有隱私之處只有浴廁,但固定時間的安檢和點名避免了病友在其內久留。這樣的環境雖然讓男女性交之事很難發生,但對於在隱密處的親熱、同性間的性行為等,其實也只能看到一點管一點。
我在 A 院曾見過一對年輕男女因接吻而遭判情緒不穩定,強制施打鎮定劑後關入保護室。事實上,這類事情又是前述那種將病友視為較一般行為人低下的潛規則,因為在一般社會常規中,只有未成年人 (不具行為能力)才會因為與異性有親熱的舉動而受到處罰 (剝奪身體自主權或行動自由)。此外,同性(尤其女女)之間的性遊戲往往不被當一回事,但這類性邀約的發生頻率其實搞不好不亞於異性之間;雖然我只能由自己的觀察出發,但我本身在兩次住院期間就都有見到。
十二、 雜談:保健室
保護室的概念就如同監獄中的單人牢房,是一個密閉的房間。當病友做出違反規定的舉動時,就可能被「請」進保護室。A 院和 B 院的保護室相去甚遠;一者裡頭有 (你在電影裡看到那種) 能將病患五花大綁的束縛床,另一者只是一間牆壁和地板鋪滿軟墊的房間。除了違反規定的病友外,也有包括我在內的患者會主動要求進保護室。進去幹嘛呢?通常是為了排解自殺/傷意念。B 院提供進保護室的病友拳擊手套和頭套,以免在敲打撞擊牆壁和地板時受傷,而且主動進去時是不鎖門的。
不過,我也被鎖在保護室過,起因是我破壞了床位上的公告板 (因為自殘意念強烈,手邊又找不到尖銳物,想把釘子拆出來用;那股意念帶來了可怕的蠻力,公告板還真的就被我給解體了),當下護理師怒氣沖沖地把我關入保護室。溫馨的是,也許是在監視器上看到我在裡面用頭衝撞牆壁,剛剛還極度不滿的護理師開門拿頭套進來幫我戴上。大約被關了半小時後 (我不習慣戴手錶,而院內只有幾處有時鐘,所以對時間的流逝只能全憑感覺),我終於被放出來,但是床位也已經被挪到位於護理站的密切觀察室了。這經歷讓我想起 A 院曾有一位時常做出脫序行為的病友,他曾告訴我他自己要求進保護室;不過在 B 院除了我自己之外,我就不曾看其他人進去過了。
十三、 雜談:行為能力
先前多少提過,精神病院的管理方式,在許多層面上是不將病友視為一個具有行為能力的成年人。病友不僅行動自由受限,就連身體自主權都遭到侵犯 (事實上,現在社會提倡未成年人的身體自主權,因此某些病友對自己身體的掌控權可能連未成年人都不如)。更有甚者,來院探訪的朋友須由父母篩選,請假外出也必須有家人陪 (即使在身體完全健康的情況下),這在在都是將病友的行為能力讓渡給父母家人,不僅對於那些父母就是壓力源的病友是種負擔,對那些病識感高的病友更是尊嚴的踐踏。當然,我確實也明白這些繁文縟節對部分病友而言是必須的,但這就像是回到一開始那個「是否應該強制住院」的問題;當某部分人得到了幫助,另一部份就可能受到屈辱,而線畫在哪裡,只反映了我們是什麼樣的一個社會。
此外有趣的是,病院雖然已經預判了病友不具行為能力,卻往往與病友立定各種契約,如生活公約、不自傷約定等等,病友若破壞了這些約定,將會受到相應的懲罰。在兩件事上徹底迴異的態度,恐怕還是反映了病院為了管理上的方便,所犧牲掉的「那一點」病友的尊嚴吧。
十四、 出院:訂定日期
入院的第一個禮拜是不允許外出的,醫生甚至完全不願意開金口談它。不過,在病情逐漸開始穩定的第二個星期,就必須開始一步一步為了回歸外面的世界做打算。通常,病友會從一個小時的外出開始,逐步增加到兩小時、四小時的外出;不過我因為有重要的事情(諮商),所以第一次外出就是四個小時。
外出那天我整個人異常興奮;十天沒呼吸到新鮮 (雖然是受汙染的) 空氣,覺得這種自由真是無限美好。不過久沒接觸外面的世界,我同時也感到外面非常吵雜,且覺得自己快要淹沒在資訊海中。四個小時的外出在趕場當中度過;除了在病院裡因太少走動,在外走了一點路就感到大腿異常疲倦外,我又活著 (且帶了一堆零食泡麵) 回到護理站報到。之後的幾次外出 (一樣從一小時開始算起)就沒有那麼敏感了,尤其最後當我被准許單獨外出時,每次都只像是普通的出門辦事,而唯一的差異就是回病院報到時更害怕遲到 (遲到有可能影響到之後的外出權利)。
接著,我和醫師開始談到出院。醫師表示一般而言有自殺意念的大概會住三個禮拜,而實際有自殺行為的幾乎都要住到一個月了;但我因後續有重要的生涯規劃,因此醫師特地通容讓我早點出院。談妥了日子心裡總是踏實許多,否則我在住了一個禮拜左右、病情沒有明顯進展時簡直心急如焚,滿腦想的都是出院。等到日期訂下,某些神秘的儀式又會開始進行─你會告訴已經與你成為朋友的病友那是哪個日子,然後一起數算剩下在一起的時間,並談論出院後各自美好的規劃。
十五、 出院:離別
終於逼近了那一天。在出院的前一天,我還是同樣過著那日復一日的作息:早餐、早操、吃藥量體溫、外出、麻將、晚飯、麻將…不過那一晚,我的運氣特別旺,胡了好幾輪;睡前吃藥時,護理師也對我說,恭喜。然後隔天,我一早就興奮的醒來,收拾好所有行囊 (其實只有兩個購物袋那麼多),前往護理站準備辦手續。最後要走時,護理師給了我一張病人自行外出 (上面註記:出院) 卡,剪斷我手上戴了兩個禮拜的病人手環,我就這麼走出了病院。在我離去前,某一天早上曾情緒失控,被我帶去護理站的病友擁抱了我,說:謝謝你那時的善意。
這讓我想起多年前我在 A 院出院時要對病友們道再見,他們告訴我「不要說再見,要說外面見」。我不曾再見過他們;也許是年代久遠,當年 LINE、FB 等通訊軟體都不若現在這般流行,總之,我的人生從此不再與他們重疊。這一次我住在 B 院,有幾位病友曾要求互換通訊方式;我未曾拒絕,但也認為出院後我多半不會再與他們聯繫。我沒有太具體的理由,也許只是覺得精神病院裡那個自己不太像是平常的自己吧。就讓裡面發生的一切只留在裡面,願那個出院後的我是那個我曾經想成為的人。